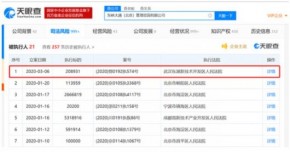(原标题:What Western Companies Need to Know About Partnering with Startups in India and China)

网易科技讯 6月21日消息,《哈佛商业评论》发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国际商务及战略学副教授沙梅恩(Shameen Prashantham)的文章,阐述西方公司在与中国和印度的初创公司合作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许多高管都在努力解决两个当代战略要务:(1)在新兴市场竞争;(2)与初创企业合作,以接触到新颖的想法和机会。这两样任务都是很难完成的,二者也共同构成了一个艰巨的挑战——一些西方企业正面临着这一挑战,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
令该挑战更加复杂的是,尽管中国和印度常常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但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全然不同的市场。如果不考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那企业在这些新兴市场的结盟初创公司战略就会出现不该有的一致性。在这两个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创业生态系统),当与初创企业合作时,企业需要采取一种更加精细微妙的方式。
在分析中国和印度的差异方面,哈佛商学院教授塔伦·卡纳(Tarun Khanna)提出过一个很好的论点。他说,印度实质上类似于像如美国和英国这样的经济体,但体制相对薄弱,也更加混乱,而中国的经济则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它的发展得到了国家更加强力的支持,因此更有条理。尽管印度明显有意加强创业生态系统,但在解决阻碍创新和创业的漏洞上,印度政府提供的支持要比中国少,也没那么成熟。
在中国,国家支持三个在推动企业与初创公司合作上至关重要的角色——生态系统协调者,生态系统参与者,以及生态系统中介者——它们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使得中国形成了某些独特的特征。首先,对于生态系统协调者,中国催生了强大的本土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塑造了企业之间追求初创公司的竞争格局。其次,在中国,生态系统参与者——包括初创企业——十分关注国家的重点发展领域,这些领域影响着跨国公司可以利用的合作伙伴的能力和发展方向。第三,培育初创企业的中国生态系统中介者(如创业孵化器)通常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努力,通过这些努力,国家政策得以落地实施。
对应于上述的这三个重要角色,根据我对中国和印度的专门研究,我建议跨国公司在中国于初创公司合作上采取三种策略来解决在这一市场遇到的独特合作机遇和挑战。这些策略会不同于它们在印度等其它新兴市场实施的策略。
与本土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与在印度不同,在中国,西方跨国公司必须要与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三大本土巨头抗衡。这意味着,吸引初创企业进入它们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许多本地初创企业将自然而然地转向BAT的怀抱。例如,在大多数主要的战场上,领先的初创公司背后必有BAT中的一家的支持;在共享单车领域,摩拜单车得到了腾讯的投资,其主要竞争对手ofo则有阿里巴巴的支持。此外,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尤其是Facebook和谷歌等将与其中一些本土企业展开正面竞争的公司——最终在竞争格局中几乎没有获得什么存在感。其结果是,在华经营的西方跨国公司不仅要相互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要与本土竞争对手展开争夺。相比在印度,它们必须要费更大的力气去实现差异化,比如在B2B商业模式上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是在B2C上。
将合作伙伴项目与国家发展重点结合起来。中国政府主导地位的一大体现是,国家优先发展领域的明确说明——例如,人工智能(AI)和物联网(IoT)——这反过来又将初创企业的注意力引向这些领域。这意味着,对于在中国寻找初创公司合作伙伴的跨国公司来说,通过物色专注于那些重点领域的初创企业,它们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而在印度没有那样的根深蒂固的模式的市场上,这样的考虑似乎没有必要。这也意味着,在中国,跨国公司将很好地确保公开宣布的合作伙伴计划能够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首席执行官布科再奇(Brian Krzanich)在深圳宣布的Mass Makerspace Accelerator项目就是很好的例子;其聚焦的物联网、机器人技术等领域,与中国的国家发展重点高度一致(比如《中国制造2025》政策)。相比之下,印度很可能会出现更多自下而上的项目,比如英特尔印度创客实验室(Intel India Maker Lab),它是在一家子公司的领导者的推动下成立的,尽管它后来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利用地方政府的政策努力。在中国,在国家层面上采取的、旨在纠正阻碍创新和创业的体制缺陷的政策措施,会落到更多的地方层面上——省一级、市级、县级等等——这通过地方政府官员经常采取的创业和创新行动来实现。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生态系统的中介者来帮助它们提高其初创公司合作项目的成效。这可能需要上海等大城市的地方政府鼓励企业参与打造张江高科技园区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或者建立起自己的创业加速器。以微软为例,中国是唯一一个它有设立第二个加速器的国家。作为推动与初创公司合作的手段,其他政策努力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有效),比如IBM在相对没那么有名的宁波市通过“智慧城市”项目与当地初创企业开展合作。相比之下,在印度,跨国公司倾向于与私营部门实体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比如通过软件贸易机构Nasscom的10K Warehouse项目与Nasscom合作。
总而言之,尽管在任何一个新兴市场都需要制定独特的战略,但就中国而言,由于国家对生态系统协调者、参与者和中介者方面的深入影响,在当地的战略很有可能会比在印度的战略独特。当然,随着印度政府寻求推出新的政策措施,从今天的中国或许可以瞥见明天的印度——但这些政策的效果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会显现。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西方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抓住前所未有的与初创公司接触的机会,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采取多适当的独特战略接触这些市场。(乐邦)